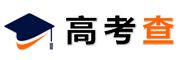袁枚诗学的历史意义及对清代诗学的影响
一、 对学人诗的反思
袁枚性灵诗学在乾隆后期的广泛影响,使当时诗坛无论是推崇者也好,排诋者也好,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它鲜明的独创性与反传统色彩,更形成后世截然对立的正负两种评价,这在王建生《袁枚的文学批评》中已有详细列举(王建生《袁枚的文学批评》第五章“当时人及后人对于袁枚和他的文学批评的批评”)。现在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袁枚诗学在明清诗论史上的意义。
日本学者松下忠曾从补古文辞格调说之短,救公安、竟陵派矫枉过正之弊,弥缝神韵说的弱点三个方面概括袁枚诗学的历史意义,认为三家诗说的对立到袁枚这里趋于缓和,形成交汇融合的特征(松下忠《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范建明译,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864页)。台湾学者张健思考袁枚诗学的时代特征,认为明代以来的宗唐派诗学到沈德潜是一个结穴,主宋派诗学到翁方纲是一个结穴,无论是宗唐还是主宋,都是趋古,而袁枚则跳出了宗唐主宋的樊篱,其审美趣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从古典诗学的立场看,袁枚诗学有其俚俗色彩,是对古典诗学主流精神的一种叛逆,其思想倾向及审美趣味显示出古典传统的蜕变,但还不属于近代的范畴,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性,是古典到近代的过渡
(张健《清代诗话研究》,第781页)。尽管这一论断很给人启发,但我还是觉得袁枚诗学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他天才论的思想方式,将诗学的关注由外在规范和技巧引向内在的主观条件,同时也使批评由基于客观标准的得失评价转向出于主观趣味的鉴赏。这不仅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重大转型,也标志着文学的时代划分。W.J.贝提在他的《批评阐要》中划分西方文学批评史之古典和现代的依据,正是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思潮的立足点由外在的绝对标准转向内在的主观条件,即柏拉图的“理念”为卢梭的“情念”所取代,从而开了主观主义批评的先河(Watler Jackson Bate,ed. Criticism: The Major Texts. Enlarged ed.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中西文学思想、批评史在此出现惊人的相似,同样是在十八世纪的乾隆末年,袁枚的性灵诗学开启了中国批评史的一个*。
不过这些对袁枚来说都太遥远了,不光他本人不能预见,就是生活在后一个世纪的论者也不会理解,袁枚嵌入古典诗学乃至文化史如此之深。
还是让我们回到乾隆时代。根据我的考察,袁枚成为诗坛重镇并产生重要影响是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前后。学界一般都将袁枚的性灵诗学视为沈德潜诗学的反拨,说“袁枚与沈德潜论诗的根本分歧,其性质实际上是一场创新与守旧之争”(严明《中国诗学与明清诗话》,第419页),从后设的角度或许也可以这么看,但如果回到历史过程中,则袁枚与沈德潜的交锋只能说是虚晃一枪,略比划两下就收手了。他清楚风烛残年的沈德潜已不足以成为他的对手。所以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高密诗人李宪乔“忧近今诗教有以温柔敦厚四字?人者,遂致流为卑靡庸琐”,希望袁枚与他一起挺身而出,共挽狂澜时,袁枚根本不认可他的想法,说:“夫温柔敦厚,圣人之言也,非持教者之言也。学圣人之言,而至庸琐卑靡,是学者之过,非圣人之过也。足下必欲反此四字以立教,将教之以北鄙杀伐之音乎?”在袁枚看来,诗教本身并不错,只不过被一群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他最担忧的是,“近今诗教之坏,莫甚于以注疏夸高,以填砌矜博,捃摭琐碎,死气满纸。一句七字,必小注十余行,令人舌口?而不敢下,于性情二字,几乎丧尽天良。此则二千年所未有之诗教也,足下何不起而共挽之?”(袁枚《答李少鹤书》,《小仓山房尺牍》卷八,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5册。又见李宪乔《与袁子才论诗教》,《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47册)时已七十九岁的袁枚,亲历乾隆诗坛由格调诗风渐趋于学人诗风的转变,对乾隆后期流行的以考据入诗的风气深恶痛绝,以为力摒这种习气才是挽救诗教的当务之急。当时学人之诗的代表不光有翁方纲等一批京师达官,还有厉鹗等活动在江浙一带的浙派。学界都认为袁枚对“夫己氏”的批评是指翁方纲,却很少意识到袁枚对浙派诗的不满。《随园诗话》提到其乡人的浙派诗,从来都没有好评。如卷四言:“陆陆堂、诸襄七、汪韩门三太史,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袁枚《随园诗话》卷四)所以当李宪乔复函挑明前札是针对沈德潜而发时,袁枚更觉得很无谓:“当归愚极盛时,宗之者止吴门七子耳,不过一时借以成名,而随后旋即叛去。此外偶有依草附木之人,称说一二,人多鄙之。此时如雪后寒蝉,声响俱寂,何劳足下以摩天巨刃,斩此枯木朽株哉!”(袁枚《再答李少鹤尺牍》,《小仓山房尺牍》卷十,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5册)相比赵执信之于王渔洋,落水狗勿打固然是袁枚宅心仁厚之处,但根本在于,他认为学人诗才是一代诗运隆替所系。近日诗教之坏的焦点??“于性情二字,几乎丧尽天良”意味着明代以来流行的“诗以道性情”之说已失去规范诗歌本质的力量,“性情”概念更是已陈之刍狗,毫无内涵的空洞概念。因此他重新拂拭“性灵”这一同样古老的概念,以取代“性情”。从这个意义上说,袁枚与乾隆前期的性灵派诗家,虽然都用性灵论诗,基本观念相通,但两者所处的诗学语境、所面临的对立面是不一样的。后者面对的是神韵诗风和格调诗风,而袁枚面对的却是翁方纲代表的学人诗风。袁枚的性灵诗风应该比学人诗风兴起得更早,但《随园诗话》作为性灵派的理论总结,写作、出版却远在学人诗风兴起之后。它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刊行十六卷本,五十七年刊行补遗四卷,嘉庆元年(1796)刻完补遗八卷,直到袁枚下世后家人才陆续刻成二十六卷足本(黄一农《袁枚〈随园诗话〉编刻与版本考》,《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9期,2013年11月)。这一过程正是袁枚与李宪乔论诗的前后几年,其中对“性灵”的诠释体现了乾隆末袁枚对学人诗流弊的反思及理论对策。这是我们谈论袁枚诗学及乾隆朝诗学的历史展开,首先必须意识到的问题。
二、 对同时诗家的影响
袁枚门人孙原湘曾说:“吴中诗教五十年来凡三变。乾隆三十年以前,归愚宗伯主盟坛坫,其时专尚格律,取清丽温雅近大历十子者为多。自小仓山房出而专主性灵,以能道俗情、善言名理为胜,而风格一变矣。至兰泉司寇以冠冕堂皇之作倡率后进,而风格又一变矣。近则或宗袁,或宗王,或且以奇字僻典阑入风雅,而性灵、格律又变而为考古博识之学矣。”(孙原湘《籁鸣诗草序》,《天真阁集》卷四十一,嘉庆刊本)这里将袁枚主导诗坛的时间定在乾隆三十年(1765),与我的结论相去不远。从孙原湘的叙述可见,性灵说最初只是在江南流行的诗学思潮,但很快就成为当时诗坛的主潮。而到他写作该文时,袁枚诗学“专主性灵,以能道俗情、善言名理为胜”,已成为诗坛的一致看法。何承燕说“近代谈诗者好尚不同,彼此龃龉,各持偏见,惟简斋太史论诗最为得中”(何承燕《春巢诗钞》自序,嘉庆二年刊本),应该代表着诗坛相当一部分作者和读者的看法。当时及后来拥趸及响应性灵说的著名诗人,王英志先生曾举出蒋士铨、黄景仁、李调元、陈文述、宋湘、法式善等人(王英志《袁枚》,《扬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程美华《乾嘉之际诗风的异动??以孙原湘与袁枚关系为例》,《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这里还可以补充杭世骏、程晋芳、洪亮吉、张问陶、方薰、吴文溥等。王文治也被袁枚引为论诗同调(袁枚《随园诗话》曾再三引述王文治论诗